马忠
申瑞瑾的散文集《千年一瓣香》收录了24篇散文,以细腻的笔触,将故乡的物件、人情与时代的流转一一铺展笔下。在这些看似寻常的乡土故事中,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亲人的牵绊,更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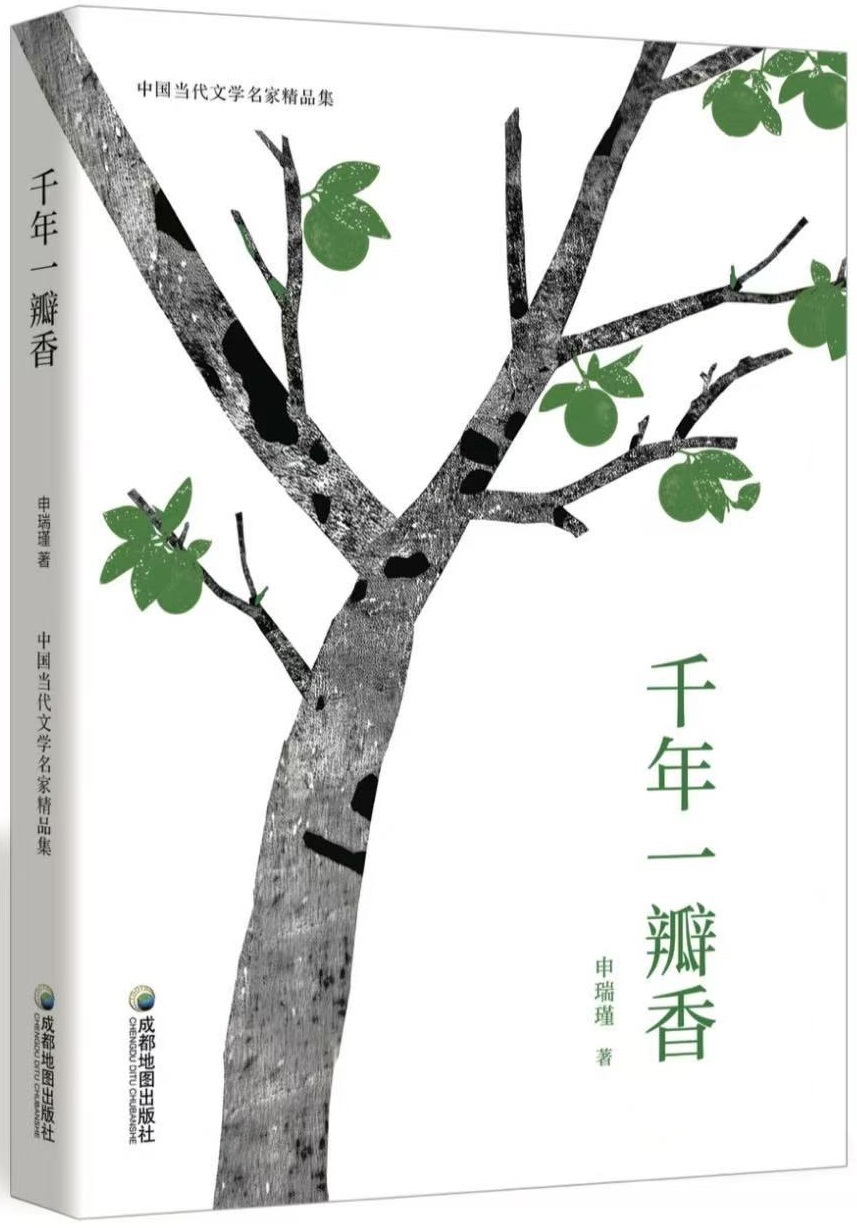
乡土符号:承载集体记忆与生死哲思
在申瑞瑾散文中,“千年屋”是最鲜明的乡土符号。这一溆浦人对棺木的称呼,不只是器物,更藏着当地人对生死的理解。
在《千年屋》里,作者回忆9岁那年,在英家楼梯间撞见“千年屋”,裹着一股孩童读不懂的肃穆,吓得她慌忙躲开——这物件于她而言,是全然未知的恐惧。严老师猝然离世,灵棚里那具“潦草简陋”的“千年屋”,让她明白这是生命终结的容器。
从恐惧到懂得,从旁观到亲历,“千年屋”伴着作者理解死亡:它像沉默的见证者,把“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的俗语,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终章——死亡不再抽象,成了乡土习俗赋予形态与温度的归宿。
溆浦的方言与习俗也织成乡土符号网。娘娘(祖母)、嫚嫚(姑姑)等带着老音的称呼,是方言对家族伦理的编码;“边唱边哭”的挽歌,从古时《蒿里》传到现在,在悲声里讲逝者生平,让哀悼成了集体记忆的传递。琐碎符号筑成乡土社会的精神根基:既是个体记忆的锚点,让漂泊的人凭一句方言、一个仪式就能回到故乡的伦理里;也是集体文化的纽带,把一代代人的生死经验连起来,成了超越时空的对话。
书中其他篇章的乡土符号同样丰富。
在《红豆的语言》里,海红豆从王维诗中的“相思”意象,变成作者手中“鲜红的小心脏”,承载着对友情、亲情乃至家国的多重情愫。在簕山古渔村和澫尾岛,红豆既是收获幸福的幸运符,也是连接古今的情感媒介,让“此物最相思”的千年诗意有了具象依托。
在《海桐花开七里香》中,海桐花(俗称七里香)与席慕蓉诗中的意象重叠,细碎白花的郁香成了乡愁的载体,“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郁香”,让年少离别与成年乡愁在花香中交融。
乡土人物:时代洪流映照生命韧性
申瑞瑾笔下的乡土人物,绝非扁平符号,而是在时代洪流与乡土根系中生长的鲜活个体。他们的命运与溆浦山水、习俗缠绕,在苦难与变迁中迸发着生命韧性。
祖母是叙事的精神核心。这个邵阳女子的一生,是一部微缩的乡土女性生存史:12岁做童养媳,21岁丧夫,4岁的儿子被叔祖父收养,夫家让祖母娘家帮她改嫁,她在动荡中拉扯大两代人,“低眉顺眼”里藏着惊人隐忍。对“千年屋”的坦然、对子孙的疼爱,让她成为最温暖的乡土印记——像石缝里的野草,根扎土地,始终向阳。
其他人物各有乡土底色,共成时代众生相。阿婆一生“精明小气”,临终却向往西湖,显露出柔软;让儿媳轮流伺候,搔痒时只肯让“我”挠,别扭里藏着亲情渴求。外公无照片留存,却以“给乞讨人盛饭必从锅里舀”的善举,在街坊记忆里成传奇;严老师作为“半边户”独撑全家,意外离世让人担忧“师娘怎么办”,道出城乡夹缝中普通人的无奈。
乡土变迁:记忆与现实的碰撞交响
在申瑞瑾的散文中,乡土变迁不是宏大的时代叙事,而是渗透在街巷气息、器物更迭与观念流转中的细微脉动。那些消失的空间、更迭的习俗、转变的观念,构成记忆与现实碰撞的和弦,既带着旧时光的温度,也映照着新生的必然。
物理空间的消逝最直观。曾摆满“千年屋”的居民点,转眼成了农贸市场,那些旧棺木“散落各处,不知所终”,像被冲走的乡土记忆。外婆住过的犁头嘴窨子屋、后院那口“涨水变浑、天晴转清”的井,连同吊脚楼、碗儿糕摊,都随房主返城而淡去;夏家溪的砖屋,曾摆着祖母的“千年屋”、回荡着跑儿的哭闹,最终也被卖掉,换成怀化的新居。这些空间的消亡,不只是砖瓦坍塌,更是乡土生活场景的瓦解——凉床上数星星的夜、天井里听吵架的日常,都成了梦中片段。
比空间更深的是习俗与观念的转向。溆浦“花甲之年割千年屋”的传统,在父亲这代有了新解:先寄存棺材,后因“大舅家不顺”卖掉,改买殡仪馆陵园的双墓,坦然说“火葬,省点土地”。这转变里,有对旧生死观的疏离,也有对现代规则的接纳。清明挂青从花果山添土,变成公墓前“点三炷香、放束菊”的简洁;祖父、父亲两代人对身后事的态度,正是乡土与现代观念的碰撞。
作者写变迁,带着“理解式的怀旧”。为祖母的墓及碑不如婆母的豪华怅然,梦里回夏家溪老屋,为外公没留照片遗憾——这是对乡土根脉的珍视。日照董家滩村变身东夷小镇,传统渔村“拆一片旧村,带一片产业”,渔民成了客栈经营者,烤海鲜香取代鱼腥气,展现了乡土空间在现代旅游浪潮中的转型。在这些变迁里,既有旧渔网与新商机的冲突,也有古歌谣与新观念的融合,如作者所言:“就像溆水会改道,却始终滋养两岸的生灵。”
总之,申瑞瑾的乡土抒写,以个人记忆为切入点,通过对乡土符号、人物与变迁的细致描摹,构建起一个真实而温暖的乡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将生命、亲情与时光拧成一股坚韧的绳,一头系着故去的亲人,一头牵着现世的生活,让每一个字符都浸透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与思。
(《千年一瓣香》,申瑞瑾著,成都地图出版社,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