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忠奇
诗歌的表达艺术取决于心灵的丰富程度,一个丰富的心灵会让文字散发出迷人的色泽。而诗歌作为最活泼、最自由的文体,能够将一个人的阅历、积淀、才情尽情地表达出来,挥洒出一方天地。赵荣刚在多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善用自己喜爱的表达方式,不紧不慢、无欲无求地面对每一首诗歌的创作。其诗集《边地》(团结出版社出版,2018年1月第一版)《边城》(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汇聚了他在边地、边城叙永生活的心灵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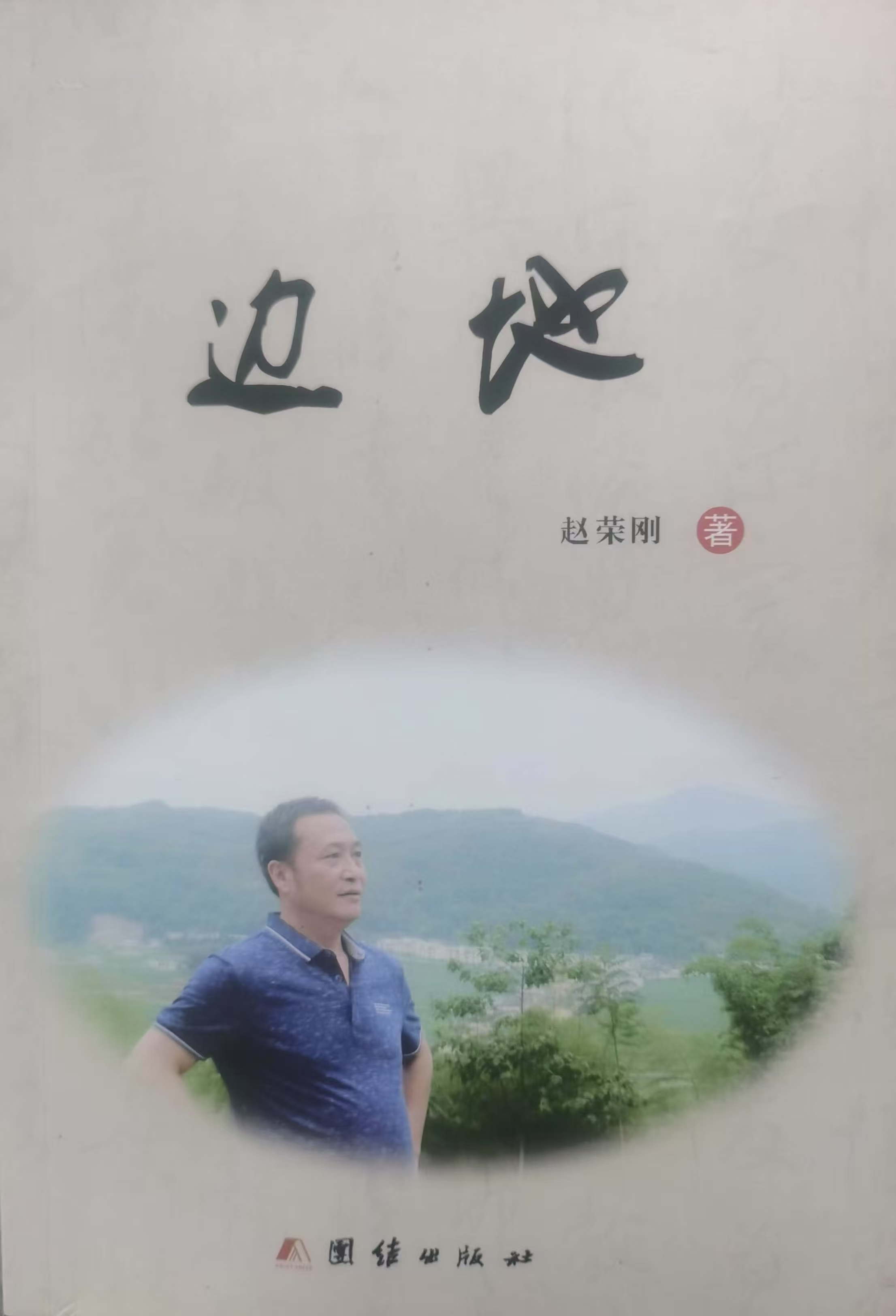
赵荣刚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忠厚的乡土使者。他对传统诗赋有较深厚的造诣,又钟爱于现代诗歌创作。他很谦逊,从不把自己当作诗人看待,正像和他一起喝茶聊天一样质朴、随意、直爽。他谦逊、恭谨的处事姿态,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不经意间让诗兴有感而发,正如他的《大雁山》中“故乡的山峰/耸立成我童年的仰望、感召着生命”所描述一样,他的每一次感动,甚至都可能触发其诗的灵感,“仿佛听见沉重的脚步/穿越楼群的峡谷/在秋风中寻找阳光/穿越枫林曾经的栖息地”(《秋风中,忽然想起杜甫的诗句》),这不仅是对社会发展中一些问题的反思,也是心灵深处某种悲悯情怀的抒发。他在滚滚长江的岸上,“隔着江面/有神魂不守的目光/搜寻梦中飘然的黑发/如浪花涌现的羽毛/拓印在心底成为梦中的图像”。生活的爱恋,对一个诗者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也正是他深沉的阅读和经历的感想,构成了他独立的诗歌视界。
一个真正的诗人能奉献给这个世界的文字,与他的思想,对待世界的态度,进入文学的角度、素养以及内心的丰富有着必然的联系。赵荣刚生活在四川泸州,成长在乌蒙山区,他的诗歌与川南叙永传统文化环环相扣,秉承独特的传统品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边地、边城,也曾有过风起云涌的现代诗歌非主流思潮,而他并没有在诗歌认知结构中形成盲目的追风定式,他始终坚持着一股质朴的创作力量,秉承着“诚信、豁达、素雅”的艺术理念,无怨无悔地在《边地》《边城》上坚持不懈地走了下来,成为一路上的风景。比如《灵应山》:
耸翠着直上云天的雄姿
左手搭在高原肩膀上,傲视天府之国
右手牵着狮子和老虎
护佑普市,保佑盐马,目送远古延绵的征途
在叙永普市村古老的边地驿站遗迹上,捕捉和感受到几百年前历史中走过的盐马的辛酸。让他在《秋风中,忽然想起杜甫的诗句》——
不老的丹山上,我俯视边城与楼群
在不朽的秋风中,我仰望土地和村庄
城市上空的飞烟和流云相遇,纠缠着四季
黄沙走石与河水相拥,相互倾诉忧伤
诗歌是赵荣刚面对现实生活的意象表达。他在《我和你栖居边地》中传达出对边地的热爱,对爱情和生活的朴素追求:
我和你栖居边地
每天做着你的事情,我做着我的工作
互不相干轨迹,到达同一个地点
你像走过的花朵,我像消磨光阴的泥土
在一首极富哲理性的诗歌《阅读者》中,他这样定位自己:
把我的目光
留下一道口子,乐在其中
品读人生文字
把我的情感
刻出一道口子,爱在其中
仅剩无悔前世
一个处事厚道的人,所写的诗歌也是脚踏实地的。
许多诗人和读者都有这样的认识,意象的“简单”和“朴素”,是诗歌创作的境界之一。这话听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实践起来,不是一件易事;没有很好的写作训练,没有复杂的积累和丰富的沉淀,不能陶冶豁达的心灵,更难抵达“简单”“朴素”的境界。像赵荣刚这样,业余时间能够这么多厚积的诗歌,也并非易事,但他还在继续努力探索着。
《边地》的绝大多数篇章是建立在亲情、家园、记忆和咏叹的氛围中。诗人在吟咏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同时,也吟出了熟悉的人、事、物之间生机勃勃独特的情感,让他的《边城》、《边地》不仅读起来有灵动性,真实感,有生命力,而且能够打通和读者之间的隧道,让读者与他的诗歌一起思考。随便选取其中的几首,便会被带入清香、氤氲的梦境中——
一位大山的美人,如云的秀发/绾在头顶。如唐宋诗词里走出来的舞女——《灵应山》
翻过横贯南北的山梁,了望茫茫的乌蒙旷野/云雾迷朦,耸立千仞的天台/南去远上云贵高原,你的栈道已成为传说的历史——《清凉洞》
这个春天。你把你的故乡放在/我的梦里发酵。同桃夭站在一起就是证明/这个春天。我把我的故乡放进/你的诗行里面。同你一道徜徉在田园风景——《故乡人》
一位农人/粗粗的呼吸,经过阳光和梨雨的缝隙/山路窄小,只容下他朴朴的身子/在纵情的季节相遇——《听花开的声音》
他最近的一首现代诗《游子》,仅有八行,却把乌蒙山区的故乡写到一个难以忘怀的诗歌意象中:
一株冬天的梅,需要一片白雪。
一只向南孤飞的雁,穿过一片白云。
我的身影,依旧是乌蒙山的白果树。
黄色的叶片飘进,春天的灵魂。
梦幻的山路,延伸川南的天空,
默默赶考的足音,消失在季风里。
故乡是父母等待的眼神。
翻过了山梁,看透游子一生的故事。
拥有丰富、豁达的心灵,就能够创造出不老的诗作。赵荣刚的诗歌情怀散发出年轻、迷人的色泽,因为“故乡是父母等待的眼神”。
作者简介:邵忠奇,泸州市古蔺人,四川省作协会员,写小说、散文,和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