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泽永
莫言在其长篇论文《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公理”,即,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凡是敢于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试身手者,如新近出版面世的《渊之光》的射洪作家高余,便是值得让我们为之致敬。长篇小说《渊之光》,是作家历时五年的一部心血之作。尽管高余曾经在诗歌、小说和评论等文体创作方面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当他确定要写作《渊之光》时,也便注定了自己必然要面对双重考验。好在,他经受住这些考验,并以其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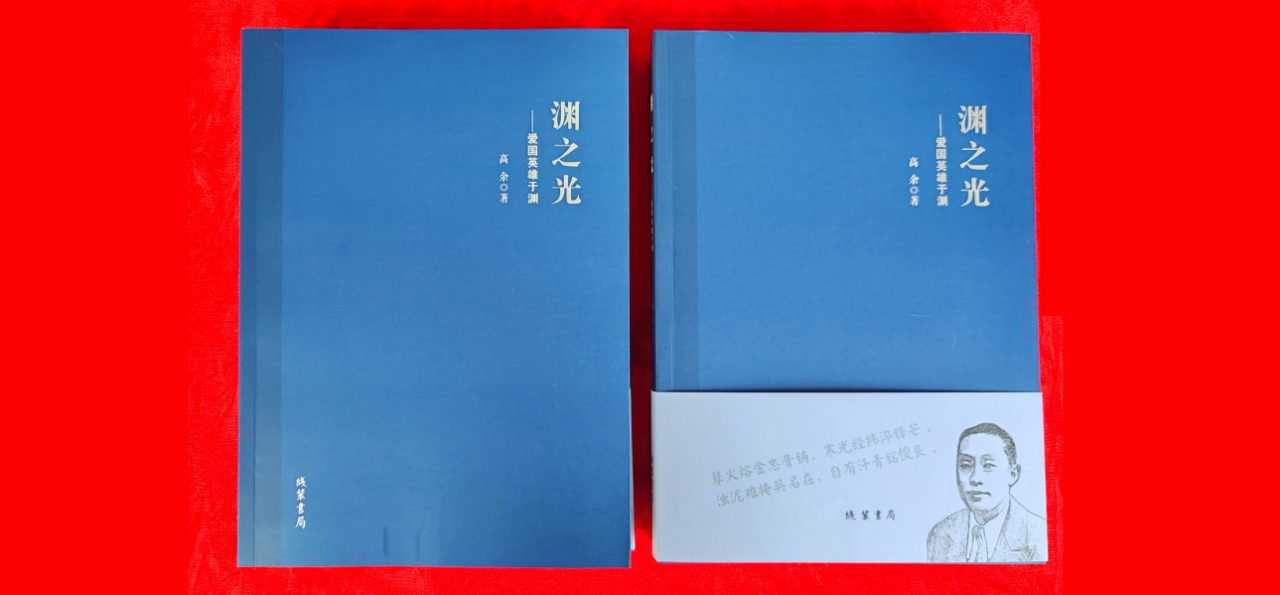
一、作者面对的双重考验
新体裁与大体量——考验创作者在自我突破中表现出来的驾驭题材、把控节奏和经营文字的能力。创作,因为习惯或长时间的坚持,容易在某种或某几种文体上形成一种定势,如果此时要去面对一种新的文体,尤其是像长篇小说这样的体裁,就一定是在面对一种新且严峻的挑战。高余在写作《渊之光》之初,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他要进行的是一种从平房到楼房、从多层到高层建筑似的尝试和自我突破。从短篇到长篇,决不应是单纯字数堆砌的量变,而应该是其《人物表》中所列93个人物活动的质变的文字世界;而要让至少93个人物的舞台异彩纷呈,这就注定了绝对不是小体量的文字可以承载的。事实是,高余用《渊之光》50万字的体量,做了最好的回应。
新题材与大主题——考验创作者对史实的搜集、梳理、提炼与逻辑推演和想象的能力。高余要面对的是一个历史题材,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载入史册的爱国英雄。尽管对史实和人物所经历的北阀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不陌生,但要具体到于渊在"万县惨案"(史称"九·五"惨案)、“清党”运动、四川省城警政与治安、配合红四方面军转移、出川抗日以及后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关心射洪家乡修第一条乡村公路、创建射洪民盟基层组织,以及被捕、就义等等一系列人生经历,这可就不是浅层的、一知半解就可以应对的。说到底,高余必须对多个特定时期的重大史事,即宏观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事件经过,了解熟悉程度要高;对被赞扬为"民国以来,中国军人对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于渊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即微观的活动与生活的细节,掌握与想象能力要强。事实是,高余用《渊之光》生动的故事,诠释了特定的历史题材和重大的现实主题。
二、作者作出的不懈努力
《渊之光》50万字的文本告诉我们,作家为此作出的努力,是艰辛而有意义的。一是他有明确的认识。作为本身就是民盟盟员的 高余深知,于渊 “既是民盟盟员,也是中共党员” 的双重身份,并非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革命力量协同的缩影,其身份意义既体现在各自政治角色的使命担当上,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中的重要价值。因此,一开始,他就以民盟盟员作家的身份自觉,把讲好于渊的故事作为使命来扛在肩上,把创作于渊这部长篇小说当着一次挑战来磨练自我。二是他有合理的定位:他在《后记》中明确地说:“我要把一个英雄用平民的视角和普通的眼光写得有血有肉。”也就是,他动笔之前,就立誓避免脸谱化、概念化,要写出人物的精气神,把人物写活,写得让其音容笑貌始终如在读者目前,并让其从而受到深深的感染。三是他有艰辛的付出:基于认识和定位的深度考量,高余知道,自己要完成的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实小说,史实是生命,艺术是质感,两者必须要有机而完美的结合融合,于是他广泛搜集资料,如电视剧本《烽火人生》、《民盟射洪县志》、纪念文集《浩气长歌》,大量购买书籍,如《中国军阀词典》《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民国军事地图》和《中国共产党简史等》等20余种,并进行实地走访采访,足迹遍涉于渊老家及其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从灵魂深处的触动,到明确的思想认识,再到搜集史料、提笔为文、几易其稿,不懈的努力,艰辛的付出,像让一粒粒沙,凝成一块块砖,最终让《渊之光》成为了一座楼,高余用心血回应了自己写作的初衷。
三、作品呈现的艺术质感
在材料处理上,避免了机械的堆积。文本中看不到作者搜集来的资料的痕迹,比如,于渊出生后,因为其母患肺结核怕传染,就交由其姑妈于续霖喂养、于渊杀了王八(王舵爷)后潜逃、其后与海哥一路上的遭遇,在刘湘部队的经历,包括在万县“九.五”惨案的向外强开枪、在成都治警、出川抗日、回射洪创建民盟基层组织,组织修建第一条乡村公路,直到最后被逮捕和遇害于成都十二桥,等等,所有的史料都被安排在生动的故事里面,一点没有生硬罗列感觉。
在细节调动上,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比如,在写到于渊刚刚接触到贩卖香妹的王八(王舵爷之前)时,这样写到:“我一脚碾压其胸,将这段时间以来积聚在心的痛苦奉还给了这个王八蛋,老子叫于渊,是香妹的大哥!上次挑粪你还讹老子一条肥猪钱,眨眼工夫你就忘记了!再不老实,马上弄死你!”这一简短的描写,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是小说中于渊的一段话,而这段话,不是于渊当年的原话,而是作者高余想象出来的,但放到故事里,我们没有感觉是作者在说,而是人物于渊在说,为什么呢?因为,高余的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游离在人物当时情境之外的,那么,这个想象就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物性格和此情此景的。于渊对香妹的爱,对王八的恨,和敢作敢为的担当,都瞬间跃然纸上。正是因为有这样合理想象出来的丰富细节描写,才使于渊及其相关的人物形象,显得血肉丰满,而不是概念化、脸谱化的那种人物。
在结构安排上,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小说分为上中下三部。而且三部的标题《湿度之经》《经度之经》和《纬度之经》,从字面的形式上看,它具有一种对称性和意蕴的深埋与外在的启发。“湿度”和“经度”、”纬度”,显然都是比喻,我揣想,作者,是要以“湿度”喻其人物于渊,早年生长生活于涪江梓江两江汇合这个特殊地理环境中,被其特殊民俗民风的滋养,既有朴素的情怀,又有血性的烈度,是其后来成为爱国英雄的重要根基。而”经度”、”纬度”,既喻于渊人生经历的纵横交错般复杂丰富,又喻其有经天纬地般的才能。这种构思,就为书写于渊“这样一位民国以来,中国军人对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做好了一种框架上的合理预设。此其一。其二,在具体展开书写时,作家采用的视角(叙述人称)也非同一般。除第一部开头“引子”的三行文字,是一个类似“全知视角”外,其余50万字,几乎均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这样的“半知视角”。而这样的“半知视角”又分为三个层面:从第一章“引子”之外起,一直到(第三部《纬度之经》)第375页第四自然段末,都是通过于渊的四姑于续霖和其徒弟陈本银,看于渊的日记的全过程来描写的。直到这二人都因于渊没纸没笔没能再续写日记离世时,其后的10页(即最后10页),是于渊的儿子民权以“我”的口气在写。但其实,大多是于渊在以“我”的视角“记”(日记)和以“我”的口气“说”(探监时口述)。小说采用这种视角的好处在于,以亲历者的视视角、口吻叙述,就极大的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感染力和带入感,从而较好地达到引起读者共情共鸣的艺术效果。
在语言运用上,体现了较好的功底。小说语言总体呈现娴熟自然的特色,增强了阅读的流畅感。无论是描写于渊带兵抗敌实战的场面,还是写他跟妻儿一起的生活细节,写给穆瀛洲等战友讲述早年在老家于家坝的故事,还是写于渊被捕时家人和朋友的反应,都因其较好地贴近了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场景而显得朴实。即使在写于续霖和陈本银两人读于渊日记时,也结合着具体的内容和阅读背景,运用恰当的语言表现了情绪情感的复杂和变化。语言的流畅感,既源于作家对人物和事件的熟悉,也源于平时的积累和着意的追求。
由此,作为爱国英雄于渊的形象是鲜明的,其性格和思想的形成,都因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得到了艺术性的诠释,充分体现了《渊之光》的创作,作为书写爱国英雄于渊的首部原创长篇小说,其创作的借鉴意义和作品的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因为《渊之光》是作为长篇小说“新手上路”后的一部作品,在其锋芒初露,彰显出作者身手不凡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些许的不足。一是小说的轮廓或框架过粗,只分“部”而没有类似“章”和“节”的呼应,降低了层次的清晰度;上中下三部的名称过于概括而略显费解;叙述者的转换或过渡的处理艺术性稍弱。这些给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或障碍。二是细节描写有过细之处,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描写,还有待强化。但尽管如此,比起小说的成功之处,这些仍属瑕不掩玉。而且有此开局,作家未来的创作,一定是大可期待的。
作者简介:
董泽永,四川省作协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