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
乡土散文是地域文化的鲜活注脚,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与人文情义。徐玉财的散文集《富顺友谊》,以川南千年古县富顺为根,用61篇亲历性文字串联起当地的人与事。全书以“情义”为核心,勾勒出富顺人的集体人格。笔者将从作者与书、文化价值与创作启示三个方面,解析这部作品如何以朴实笔触书写乡土情义,成为记录富顺文化的“活态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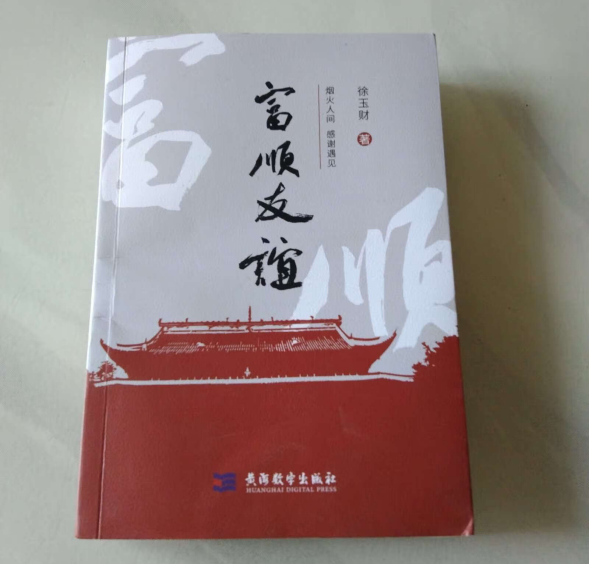
一、作者与书:浸满富顺烟火的情义载体
徐玉财是“富顺本顺”的写作者——一辈子未远离这片土地,脚沾富顺泥巴、口食富顺豆花,笔下自然是富顺的人与事。年轻时,他做了20年基层教师,日日扎根乡村学校:知晓学生摸黑上学的露水裤脚,熟悉乡亲田埂上就风扒饭的搪瓷碗钵,难忘煤油灯下改作业到半夜的叹息。这些接地气的日子,不是虚构的素材,而是他写作的来源。调入县文化馆后,他成了地方文化的守护者:非遗申报、文学采风、群众活动,事事亲力亲为。富顺非遗从2项增至12项,他全程参与;老艺人扎牛儿灯,他蹲守记录竹篾削法与布料染色;豆花师傅点卤,他细学泡豆时辰与卤水用量。这些旁人眼中的“小事”,在他看来是富顺的“根”,尽数藏进日后的文字里。
此前,他的“岁月三部曲”已收录不少富顺故事,《富顺友谊》作为第四本散文集,2025年由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收录2020—2024年的61篇文章,共25万字。书中都是他亲眼见、亲耳听、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全书核心是“情义”,分五辑串联富顺的人、景、事、情,读来如随作者逛一趟真实的富顺。书里的人都是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如文化老人伍松乔、王德海,他不写大师风范,只记茶馆里富顺市民的闲谈,或是乡村教师守着偏远学校,在煤油灯下备课的身影,或是桌上摆着学生送的野花,还有非遗传承人李师傅自掏腰包邀人学扎灯,刘师傅毫无保留传点卤诀窍,字里行间是手艺人的坚守等。这些人和事,充满富顺情义烟火气。
书里的景与物不用滤镜呈现,而是以自然写实的方式表达,我们因此听到在赵化古镇、狮市古镇的凌晨,张婆婆磨豆子的嗡嗡声传半条街;看到街角修鞋的王大爷摆摊三十年,多给钱就摆手不要的皱巴巴的老脸;看到文庙西湖的四季,是春柳垂水、夏蝉伴棋、秋叶浮波,不洋气却亲切。
二、《富顺友谊》的价值:存活文化、探新路、唤乡愁
《富顺友谊》虽非十全十美的典范作品,却在富顺文化传承与乡土散文创作中具有一定价值:为富顺存活文化、为乡土散文探新径、为读者唤乡愁。
(一)存活文化:带温度的富顺档案
在城市化加速下,老房子、老手艺、老方言渐失,徐玉财的书如文化保险柜,将这些易逝的记忆装了进去。
他写豆花做法,不是“选豆、泡豆、点卤”的干巴巴说明,而是张婆婆的实操:“挑颗粒饱满的黄豆,天热少泡、天冷多泡,点卤要慢加慢搅,直到豆浆凝固”,字里行间满是豆香;写富顺人的处世哲学,不喊“重情义”的口号,而是茶馆对话“豆花饭安逸,海椒酱巴适,再要一勺”,实在劲儿扑面而来;写牛儿灯手艺,不贴“非遗”标签,而是李师傅扎灯的细节:“竹篾要匀、布缝要密,脸谱红要艳、黑要浓”,能想见艺人手上的老茧。
更难得的是,这些内容被编进富顺中小学校本教材。孩子们读着知“豆花怎么做”“前人怎么过活”“富顺人该如何待人”——文化从不是博物馆展品,而是靠这些带温度的故事传承。四川省散文学会的钟永新老师称其为“富顺文化的活态档案”,恰因它记的不是“死知识”,而是富顺人鲜活的日子。
(二)探新路:杨德友病中日记与才哥曰双线结构
徐玉财在《富顺友谊》中改变以往的写法,用杨德友病中日记为内视角,才哥曰为外视角,两个视角,两条线索,结构内容,意在探索散文写作新路。
杨德友病中日记重点记录2007至2017年患肺结核期间的生命轨迹:既有病情反复的痛苦(如咯血、盗汗、治疗无效的绝望),也有生活烟火气(钓鱼、炒股、搬家、为儿子庆生),还包含对亲情的牵挂(担忧儿子沉迷游戏、牵挂父母安康)、对友情的珍视(与才哥等同学相聚),以及参与免费午餐公益的温暖。其特点是真实细腻,直击生命困境,字里行间满是对生命的眷恋与挣扎,兼具痛感与温情。
才哥曰是才哥对日记的回应:补充日记未提及的共同经历(如一起逛北湖、祭奠故人),体谅杨德友的自尊与孤独(如隐瞒家人对病情的顾虑),赞扬其重情重义、善良坚韧的品格,还融入富顺地域文化(豆花、西湖、方言)。特点是温情共情,以旁观者视角丰富人物侧写,填补日记空白,让杨德友形象更立体,同时传递出富顺人的情义底色,双线交织深化了友谊与生命的主题。
(三)唤乡愁:用实在事勾连集体记忆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关于 “集体记忆靠具体故事与场景攒成” 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集体记忆》的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分析中,其理论始终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场景依赖性。哈布瓦赫对 “记忆建构” 的核心主张:集体记忆并非对过去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具体的互动、叙事和场景,在当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徐玉财的《富顺友谊》暗合哈布瓦赫主张,你念老家豆花摊,我忆江边童年,他想茶馆闲谈,凑在一起便是乡愁,便是集体记忆。
《富顺友谊》出版后,孔夫子旧书网售其签赠本,“富顺才哥”公众号满是读者留言:“读沱江想起跟爸妈洗衣,水凉丝丝的”“见豆花饭描写就想回家,妈做的最嫩”“茶馆闲谈跟老家一模一样,爷爷天天去坐”。究其原因,作者不喊乡愁空口号,只写实在事:清晨后街豆花摊,街坊端碗站着或蹲着吃,吃完各忙各的;夏天沱江边,老头聊当年摸鱼,年轻人说下月回家,小孩追跑,江风送凉;茶馆里,老板知谁爱浓茶、谁爱淡茶,有人下棋、有人闲谈。这些场景藏着共性记忆——不是沱江也可能是家门口小河,不是豆花摊也可能是早点铺,不是茶馆也可能是村口小卖部。一读便念起自己的根,暖意丛生。乡愁从不是抽象的“想老家”,而是想老家的饭、河、人,《富顺友谊》恰用实在事,将这份乡愁勾了出来。
(四)在场写作:亲历与共情
在场写作以“亲历性”“语境真实性”“个体情感介入”为核心,强调作家直面现实、扎根本土,在个体与对象的深度互动中挖掘生命与文化的联结。可以说《富顺友谊》是在场写作的一种实践:作者徐玉财以富顺人的亲历视角,将自身情感与本土人事深度绑定,无论是对杨德友十年抗结核历程的细节追溯(从日记原文摘录到“才哥曰”的共情回应),还是对肖慈旭、王德海、李自国等文化守望者的近距离书写,均源于亲身接触与深度共情,而非抽象叙事。
从《富顺友谊》中不难发现,作者以豆花、沱江、文庙、方言等具体风物为锚点,串联起富顺“狡猾多端又义薄云天”的集体人格,记录非遗传承(杨氏中医、自贡灯谜)、民间文艺(京剧协会、二胡之乡)的鲜活实践,让地域文化不再是符号,而是附着于具体人事的可感存在。同时,作者不回避生命的苦难(杨德友的咯血)与文化的坚守(童昌信捐《沱江行吟图》、张新泉的诗歌守望),以“在场者”的真诚,让富顺的友谊、乡愁与文化传承,在细节与情感的交织中,成为可触摸的生命记忆与文化坐标。
三、不完美的作品:遗憾、原因与地域文学启示
毋庸置疑,《富顺友谊》也存在一些遗憾,寻找这些遗憾并探究其原因,可以为地域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一)遗憾:有真情却缺巧劲
其一,内容重复、结构散。写杨德友“咯血”,2010、2011、2016年日记反复提,作者次次写“心疼”“无奈”,多次重复易让读者麻木;“重情重义”主题较为单调、单一,写杨德友、李昭明、聂成松,都只说“重情”,未从“患难真情”“手艺之情”“朋友之情”等角度区分,显得乏味。结构上,第三辑“文化守望者”一会写肖集刚刻版画,一会写雷安邦做公益,只罗列“做了啥”,未串联故事,如珍珠散盘;部分日记节选过长,杨德友某篇日记写三页“吃面条”“天冷”“午睡”,与“情义”无关,读着易走神。
其二,人物刻画不均。杨德友写得鲜活:病重时绝望说“不想活了”,好转后乐观“明天钓鱼”,与作者争论文章的好坏,固执却真实,如生活里的老大哥。但次要人物太薄:写雷安邦“年捐10万助乡修公路、建学校”,未提他与儿女的沟通、与乡亲的分歧;写肖集刚“刻富顺古镇与豆花摊”,未写他没灵感时的焦躁、找木头的艰辛、手上的茧子。这些细节缺失,让人物成了“纸片人”,读者记不住、生不出情。
其三,视角局限、情感直白。作者只写富顺的好,避谈难题:李师傅愁“年轻人爱打工,没人学扎灯”,朋友间的拌嘴误会,年轻人“不想卖豆花,想进城闯”,都未提及,似加了滤镜,不够真实。情感表达也直愣愣,写杨德友离世,直接说“号啕痛哭”“泪水盈盈”“真的伤心”,不懂留白。若写“他常去的茶馆还留着位置,杯子里的茶凉了没人续”,或“没写完的日记摊在桌,钢笔夹页间,墨水干了”,读者自能感受悲伤,比直白喊“伤心”更有味道。
其四,混淆私人与集体情义。作者将自己与杨德友的私人友谊,直接等同于“富顺人的集体情义”。实则二者不同:“我俩好”是因共同爱好与性格,换个人未必处得来;“富顺人重情”是地域文化滋养的集体特质。二者虽有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这一混淆让“二人友谊”失了独特性,也让主题模糊。
(二)原因:“太实在”困住了创作
一是“太感性少理性”。此书为纪念杨德友而作,二人是几十年“过命的朋友”,作者舍不得删重复的日记与回忆,总觉得“多写一句,就多留一点他的影子”。但写作需理性:重复内容让读者腻,无用细节拖慢叙事,如同煮菜只放糖,失了风味。对次要人物,因感情不深便不挖细节,觉得“提一句就行”,忘了细节才是人物的“活气”。
二是“太贴地没抬头”。作者身为富顺人,熟悉家门口的豆花摊、老手艺、方言,却未往大处想:写富顺人重情,未探“是否与巴蜀‘尚义’文化、盐都‘诚信’传统有关”;写乡土文化,未关联“城市化对富顺的影响”“富顺文化在四川文化中的位置”“与自贡、泸州文化的差异”。视角太近,文章便缺深度,只能写“事”,不能说“理”,如挖井只一尺深,尝着甜却不解渴。
三是“主题先行躲矛盾”。作者想突出“温情”“重义”,便放大好的一面,躲开矛盾:避谈朋友拌嘴,怕破坏重情;避谈非遗难题,怕冲淡守望;避谈年轻人离乡,怕影响爱乡。但真实生活本有好有:拌嘴后和好更显情义,非遗难题更显坚守,年轻人离乡更显家乡变化。躲开矛盾,虽合纪念故人初衷,却丢了直面真实的力量,让文章少了厚重感,如同豆花没点够卤,嫩却没嚼头。
(三)启示:实在比完美重要
即便有遗憾,《富顺友谊》仍为地域文学创作提供了四点实在启示:
第一,“扎进生活别飘着”。徐玉财写得真,是因为他真参与非遗申报、真和富顺人吃豆花聊家常、真逛古镇看手艺,而非查资料瞎写。反观有些作者,未到当地便写“美食景点”,文字如旅游攻略,无温度。要写好地域文学,需先在当地生活:吃百姓饭、说百姓话、做百姓事,唯有真经历,才能出真感情,如同种庄稼先下地,才知庄稼脾气。
第二,“平衡私人与公共别偏科”。书中“杨德友日记(私人)+才哥曰(公共)”的写法值得借鉴,但需注意:私人叙事是“入口”,要提炼公共价值;公共道理是“升华”,不能丢私人情感。如写杨德友生病,既写“他难受想放弃”(私人),也写“富顺人遇苦难不低头”(公共);写他做志愿者,既写“给娃盛饭”(私人),也写“富顺人互助精神”(公共)。只写私人小事成流水账,只说公共道理成说教,如同豆花需黄豆与水比例合适,缺一不可。
第三,“打磨内容挖细人物别凑数”。素材要挑有用的,重复内容如杨德友日记里的琐事,该删就删;哪怕感情深的素材,也要按“叙事逻辑”留,不能因舍不得硬塞。人物刻画要均衡,核心人物挖细节,次要人物也抓特征:写雷安邦加句“乡亲嫌公路窄,他拿尺量说‘先让大家走,以后再扩’”,写肖集刚加句“捡木头打磨,手上口子贴创可贴接着刻”,人物便鲜活起来。读者看的是内容实、人物真,而非字数多、人物多——三个活灵活现的人,远胜十个“纸片人”。
第四,“情感留白直面现实别躲”。散文情感要“藏”而非“喊”:写怀念杨德友,用“他的鱼竿还在沱江边,却没人用了”,比“我想他”更动人;写朋友好,用“他总带热豆花来,知我爱吃”,比“他对我好”更真切。现实有好有坏,要敢写非遗传承的难、朋友间的吵、年轻人离乡的无奈——这些不完美不是破坏主题,而是丰富主题:李师傅的着急更显坚守,与杨德友的吵架更显友谊珍贵,年轻人的闯劲更显家乡变化。如同富顺豆花需豆花的嫩与海椒酱的辣,文章有暖有难、有笑有愁,才够真实,才让读者觉得“这是生活,这是我的家乡”。
总之,真情是地域文学的根。《富顺友谊》不是完美的散文,却是真诚的散文。地域文学无需追求高大上与惊天大事。写好身边的普通人,写好日常烟火气。说到底,写地域文学,就是写自己的根:根扎得深,文字才长得旺。
下一篇:
评冰春的抗日谍战历史小说《川江东逝水》